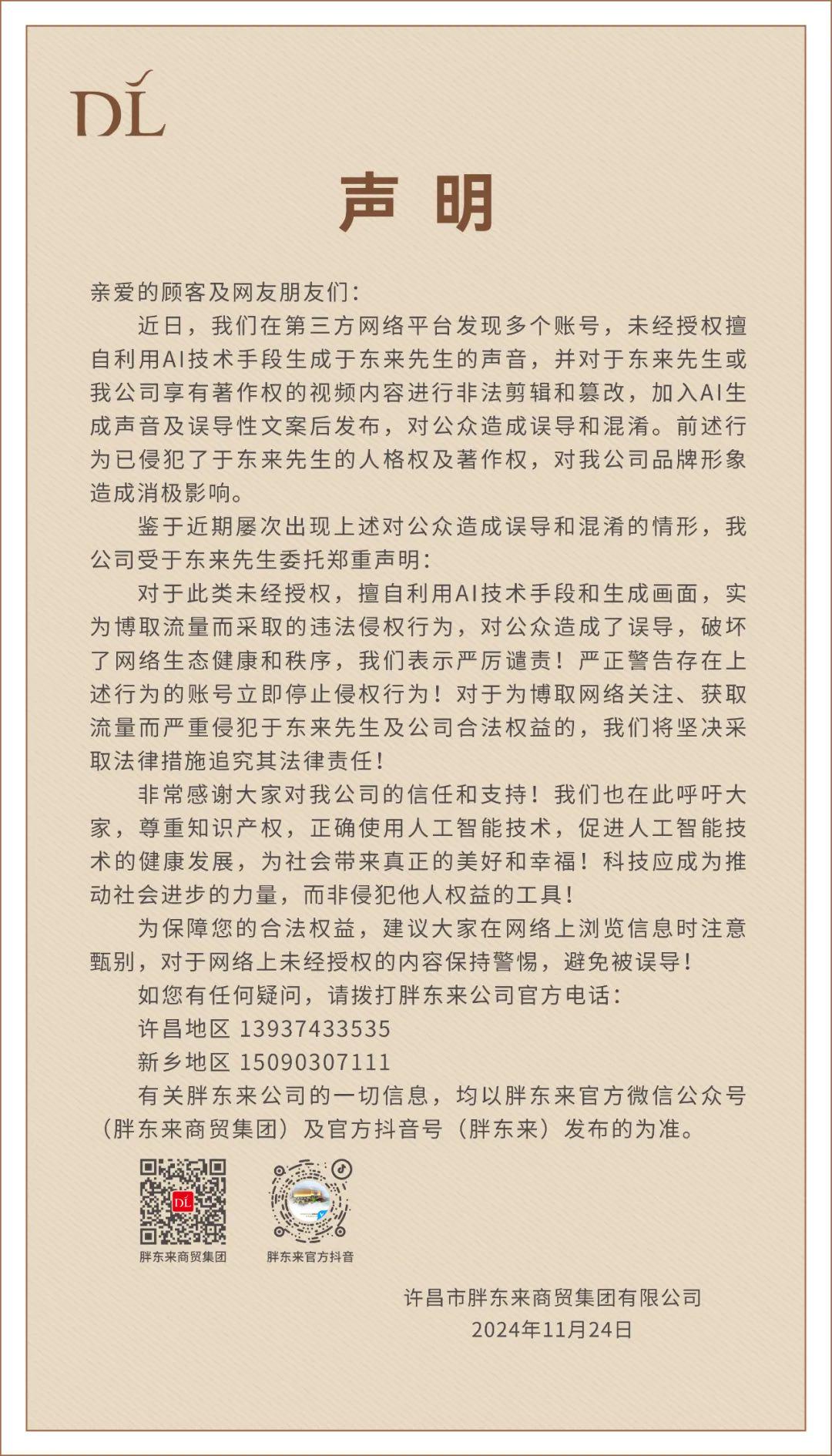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类型、量刑幅度等进行了全面修改,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刑法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国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
增加和调整犯罪行为类型。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电子侵入”获取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类型。利用电子侵入方式获取商业秘密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而且成本低,收益高,俨然已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重要形式,甚至出现了集团化和跨地区化作案的趋势,应予严厉规制。将“利诱”方式获取商业秘密修改为“贿赂、欺诈”。“利诱”作为罪状表述,具有很大模糊性,其规范内涵一直存在争议,相比之下,贿赂、欺诈的规范表述能够更加明确地确定刑法打击的犯罪行为类型。取消第三人过失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修订前的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罪包括“明知”与“应知”两种形式,即故意和过失两种主观罪过形式。然而,将第三人过失侵犯商业秘密作为犯罪打击并不妥当。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的“以公开换保护”的制度特性,商业秘密的重要特征正是其秘密性,普通工作人员往往无从得知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因而也无法判断在交易过程中涉及的商业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如果将对泄露商业秘密这一危险结果的预见义务加之于身,势必会增加交易成本甚至阻碍交易,使科技、商业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受到阻碍,进而妨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因此,修正案取消了第三人过失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降低入罪门槛,提高量刑幅度的上限、下限。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商业秘密罪的入罪门槛由修订前的“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改为“情节严重”,使得该罪的罪量标准认定更加多元化,纠正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认定中长期存在的“唯数额论”倾向,使得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危害结果可以涵盖未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却发生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况。据此,侵犯商业秘密罪已经由结果犯转变为情节犯或行为犯,这将会对司法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此种变化也被认为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修订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当然,对于“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以外的其他“情节严重”情形如何认定,立法者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判断要素,尚需司法实践进行类型化总结和概括。此外,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起刑刑种由拘役刑升格为有期徒刑,并将有期徒刑的最高幅度由有期徒刑七年提高至有期徒刑十年,此处修改与同章节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期的调整保持一致。刑法修正案(十一)提高刑事处罚力度,有助于威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删除关于商业秘密的定义,实现商业秘密侵权的民法治理与刑法治理的有效衔接。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对商业秘密进行定义的前提下,不再对其进行重复规定,既节约了立法成本,也增强了涉商业秘密民刑法律的系统性,避免民刑法律之间脱节或倒挂。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4月23日起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作出两点修改:一是将商业秘密的客体范围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扩大为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从立法技术上避免因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分类不周延造成“灰色地带”,使得技术信息、经营信息以外的商业信息在符合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可以成为商业秘密保护客体;二是删除了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中的“实用性”要件,拓宽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修改前的商业秘密要求具有实用性,即只有在商业秘密具备了现实操作的可能性之后才会受到法律保护。然而,在诸多基础性研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中间数据或成果,这些数据或成果尽管无法直接转化为现实产品,但同样具有价值,应当给予保护。况且,实用性判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刻舟求剑的问题,现在不具备现实操作的技术信息或许在未来或者其他行业领域可以应用。因此,修改后的商业秘密定义删除了商业秘密的实用性要件。
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科学立法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法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基础,也为相关领域的刑事司法实践留下了充足空间。从法治经验来看,只有通过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实现商业秘密领域的良法善治,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办理涉商业秘密犯罪案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准确把握保护法益的转向。民法典将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之一,宣示了商业秘密权的私权本质,廓清了商业秘密的财产权属性,无疑将会使商业秘密的民事保护迈上一个新台阶。在商业秘密被确认为权利以前,可以将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法益认为是一种个人法益或者包括个人法益和市场竞争秩序在内的复杂法益。因彼时民事权利设置缺位,在民事层面保护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刑法可以发挥补缺功能,为商业秘密所有人提供法律救济。现在,商业秘密被正式确认为一种民事权利,刑法保护的法益就充分关注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法益层面。从刑法体系来看,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侵犯财产罪”中,也决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所保护的法益重点就是市场经济秩序。如果司法人员仍然将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刑法保护法益界定为一种个人财产法益,就会不可避免地在入罪时只考虑权利人的损失问题,而忽略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影响规范目的实现。
二是既要厘清侵犯商业秘密民刑治理边界,又要形成民刑共建共治合力。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治理,主要包括民事治理和刑事治理两种类型,民法的规范目的在于损害赔偿,刑法的规范目的则在于惩罚和预防。民法作为规制侵犯商业秘密的前置法,应当成商业秘密保护的常态性法律,而刑法应当在适用时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和保障性,在民法力所不逮的范围,刑法才有发动刑罚制裁的必要性。
具体而言,民刑治理边界区分的关键在于对“情节严重”情形的认定。对于“情节严重”情形,应当建立起以重大损失要素为主,综合考虑企业信誉损害、企业停业等情况多元化综合认定机制。在认定过程中,关于情节严重与否的判断均应以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为标准。商业秘密进入了市场,在竞争中存在,在交易中发展,是其具有财产属性的本质原因,特别是我国民事法律采用竞争法而非财产法模式对商业秘密予以保护,刑事法律亦建立在竞争法模式的基础上。因此,在对侵犯商业秘密的损害后果进行认定时,应当以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和导向。
三是统筹兼顾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合理运用程序法功能解决案件难点。商业秘密不仅具有典型知识产权的无形性特征,而且兼具秘密性特征,大大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办案难度。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时,司法人员经常面临商业秘密定性以及损失难以界定等技术性问题,此时,要充分利用司法鉴定的程序功能。另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诉讼双方均可以申请技术调查官出庭对专业技术性问题予以说明解释,从而使合议庭与控辩双方在涉案技术性争议上的沟通更加精准、顺畅。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